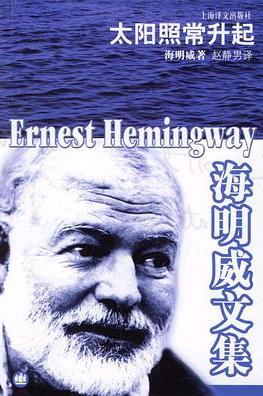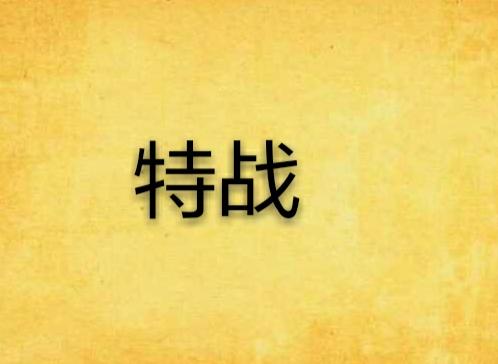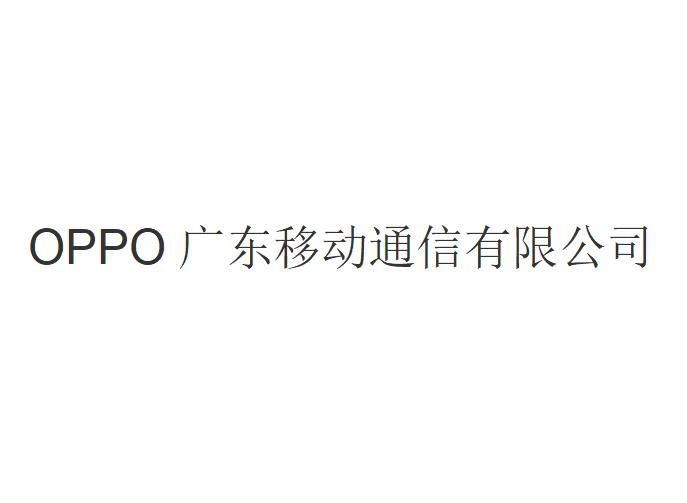内容简介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脊椎受伤,失去性能力,战后在巴黎任记者时与英国人阿施利夫人相爱,夫人一味追求享乐,而他只能借酒浇愁。两人和一帮男女朋友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斗牛节,追求精神刺激。夫人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却迷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然而,在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夫人最终回到了巴恩斯身边,尽管双方都清楚,彼此永远也不能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人物介绍
杰克·巴恩斯
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故事的叙述者和中枢人物)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侨居在巴黎,书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挚友或熟人。巴恩斯曾在意大利前线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由于受伤的部位偏巧是他胯下的生殖器,使他从此落下了性功能障碍的后遗症,因此他虽有性爱的欲望,却没有做爱的能力,无法同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
这是郁积在他心中的最大的症结,是他的一切烦恼和不可名状的痛苦的罪魁祸首,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巴恩斯深爱的女人是故事的女主人公勃莱特·阿什莱,勃莱特也深爱着他,两人相识已久,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注定让他们无法结为夫妇。由于自己性无能,巴恩斯只能坐视、容忍勃莱特在别的男人面前寻欢作乐;由于对勃莱特爱之入骨,他愿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甚至可以撮合她跟别的男人幽会,眼睁睁地让她成了他人的未婚妻或情人,然而他灵魂深处却在咀嚼着难以言说的悲酸和痛苦,这种矛盾、复杂的滋味是不言而喻的——有内疚,有心痛,有妒忌,有失意,有孤独,有无奈,有苦闷,有空虚,有屈辱,有无处宣泄的愤恨……种种禁锅了精神并使之痛苦的东西全都纠结在一起。
这种令人心碎的痛楚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巴恩斯不是英雄,而是海明威精心塑造的一位形象丰满的“反英雄”,是一个保持着“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打不垮的”的类型化角色。无法治愈的战争创伤、难以实现的爱情、不可言说的隐痛、破碎的理想,凡此种种,都没有摧垮他的意志力,不能使他颓废沉沦、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被命运“打败”的人,但是他“败而不垮”。
勃莱特
勃莱特容貌艳丽、风度翩翩,自然是男性心仪的对象。然而,她的行为,如品酒、抽烟、留短发、着短装、性解放等在当时的确具有叛逆精神。但要说明的是,这毕竟是时代使然,除喧嚣尘上的消费主义之外,更得益于女权主义的发展与弗洛伊德主义的传播。相比之下,小说其他三个男人却体现了被动、顺从、胆怯、冲动等女性特征。这就意味着,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性倒错位。勃莱特作为人物形象的复杂性预示着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女性的性别复杂性和确定性。她的迷惘表明了女性角色的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还无从定位。
罗伯特·科恩
罗伯特·科恩是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重要人物,但他是海明威刻画的一个“反面角色”。科恩是美籍犹太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曾获得过该校重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他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来巴黎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寻找文学创作的素材。他在纽约出版的第一本书给他带来了成功的喜悦,然而第二本书的写作却茫无头绪,毫无进展。他的第二任未婚妻也跟随他从纽约来到巴黎,并牢牢控制着他,但他最终还是狠心抛弃了她,转而去追逐勃莱特了。
他是在一次酒会上邂逅勃莱特的,当即就被她艳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迷恋得神魂颠倒,没多久便偷偷携她去圣塞瓦斯蒂安同居了一个星期。他满以为勃莱特从此就是他的人了,以为真正的爱情能够征服一切,还想跟她正式结婚,岂料勃莱特只是逢场作戏,事后便对他厌恶至极,视他为“一头十足的蠢驴”,甚至不屑于同他握手。这使他深感困惑,并为此而伤心欲绝。
在巴恩斯的朋友圈中,科恩是一个特例。他没有参加过残酷的战争,没有经受过精神磨难的考验,他依然还俗守着战前传统的价值观,对生活和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个陈腐的浪漫主义者和虚妄的理想主义者,与巴恩斯这伙人根本不是“一路人”,因此,他处处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令人讨厌。
佩德罗·罗梅罗
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是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位他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罗梅罗才十九岁,却英姿勃勃,举止不凡,浑身散发着年轻人的昂然朝气。他精于斗牛,技艺超群。在斗牛场上,他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优雅的风度赢得了众人的崇拜。在社交生活中,他为人坦诚,谈笑自然,从不扭捏作态。他身上既没有“迷悯的一代”的颓废,也没有科恩那种以英雄自居的虚假派头。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勃莱特,他与科恩进行了一场力量悬殊的决斗。
在拳击上,他固然不是科恩的对手,一次又一次被击倒,但他在精神上却始终是胜利者,最终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打垮了科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赢得了勃莱特的信任和钟情。罗梅罗是海明威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打不垮的”硬汉形象的代表:无论面临多大压力,始终都保持着优胜者的风度。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涉及多方面的现代小说,其反映的主题是战争在生理、心理、伦理等方面对“迷悯的一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这部“情绪结晶式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在于着力表现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于宣泄他们的情绪,展示他们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心理发展历程,并由此深入挖掘和直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这一代人所有的梦想、信念和单纯都已被战争和现实的残酷击得粉碎,人生的目标已经死亡,他们在毫无节制的酗酒和纵乐中品尝着内心的绝望和悲哀。小说中的巴恩斯集中体现了“迷惘的一代”的主要特征:他虽然头脑冷静、性格沉稳,但他已变得漠视一切,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不再相信诸如亲情、友情、爱情、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传统的希望之源,唯有纵酒宴乐能给他带来一时的快慰和解脱,即便是富有闲情雅趣的旅行,也每每成为豪饮的借口。
酗酒是这部小说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话语题材,这不仅是因为这伙饱经磨难的才子们常常“借酒浇愁”或“以酒会友”,在酣饮烂醉中暂且忘却伤痛,或借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慨,更因为这种酗酒行为本身就是对美国政府当年所颁布的“禁酒令”的公然蔑视和对抗,对父辈所遵从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说教的讥讽和反叛。
小说中唯有自命清高的科恩从不酗酒,因而与他们不是“一路人”。责任感的缺失、“对什么都无所谓”,是“迷悯的一代”的另一特征:巴恩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对工作毫无激情,总是漫不经心;尽管他偶然也去教堂,却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从不愿过问任何是非纷争,即便对能够出手相助的事情,他也漠然置之,袖手旁观。例如,在对待科恩与勃莱特之间的情爱问题上,他始终无动于衷,科恩为情所因而痛不欲生,他却不屑一顾,反应冷淡。
勃荣特则常常随心所欲地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尤以挫伤有钱男人的自尊为乐。她的未婚夫迈克对她更是放任自流,他自己也置事业与家庭不顾,常常举债酗酒,长醉不醒。海明威在感同身受地记述和批评“迷悯的一代”追求享乐、灵魂空虚的精神状态的同时,对这一代人也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并希望世人能以此为鉴,放眼未来。
泛性主义和西班牙斗牛是这部小说主题结构中并行不悖的两个组成部分,泛性主义主要体现在勃莱特身上,尤其表现在她的性爱取向上。她视自己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喀耳刻,迷人的姿色使她能游刃有余地在男人堆里周旋——在希腊伯爵米比波波勒斯面前放肆地开怀畅饮、打情骂俏;信誓旦旦地要嫁给迈克;和科恩私奔;最后又勾引罗梅罗和她上床做爱。她要追求的显然是她一心向往、但从巴恩斯身上却得不到、从前两次毫无爱情的婚姻中也未曾获得的真正完整的爱情。然而放纵不等于“个性解放”,肉欲不等于爱情。这位离经叛道的“新女性”终究未能逃脱世俗的樊篱。
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在小说中多次隐喻化地借用斗牛的场景来映射勃莱特的性爱,在两者之间进行住复式的比拟。勃莱特曾明确告诉巴恩斯,她不可能对他做出任何承诺。这就是说,她不可能恰守妇道对他“忠贞不渝”,这也意味着她很善于耍手段巧妙地让男人乖乖就范而又不惹火烧身。
回归自然、呼唤脱胎换骨的新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大自然在海明威的笔下风光措施,生机盎然,充满画面感的山川原野犹如人间天堂。每当巴恩斯置身于远离都市和女人的原生态的大自然中,尤其在富有田园野趣的溪边或湖畔钓鱼时,他就感到精神振奋,活力勃发。
和作家比尔结伴外出钓鱼时,两人更可以敞开心扉,手提酒瓶畅所欲言地谈古论今,痛快淋漓地针砭时局,即便比尔讥笑他钓来的鱼不及他的大,他也不计较,尽管他心里明白,比尔是在影射他的性功能远不如他强。在圣福明狂欢节期间,热烈的节日氛围、盛大的庆典场面、浓厚的宗教色彩、淳朴友好的西班牙乡民,使巴思斯深受感染,也激活了他对生活的信念。小说接近尾声时,巴思斯在圣塞瓦斯蒂安的孔查海湾中畅游,他时而在海面上迎风破浪,时而深深潜入海底,他既是在经受体力、耐力和勇气的考验,也是在接受大自然对他的洗礼。在小说结尾处,巴恩斯深情地拥着回到他身边的勃莱特,眺望着前方高举警棍在指挥交通的骑警,心中在无限渴望地憧憬着未来。
艺术特色
总体风格
《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海明威冰山创作原则的起始之作。在《太阳照常升起》之中他尽量采用直截了当的抒情、鲜明的对话、简短句式,用简单易懂的词语把事件、景物、人物的语言、心理描写、行动等呈现在读者眼前。
小说就是照搬日常生活,并没有从特定第几人称进行叙述。《太阳照常升起》中,作者并没有以主人公作为进行叙述对象或者做过多的描述。作品中以战后的迷惘一代为描写对象,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大人物,情节描写也似乎小太完整,时间跨度也只有短短几天。故事中一切事情就是发生如此自然,也没有刻意交代每个人物结局,把人生的横的发展方式从中切断,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窥探一个人一生。这样的描述方法仿佛是看到一个人日常生活中某一细节被记录下来,作品中的人物就像你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必要去追根溯源,一切显得那样朴素和自然。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语言运用方面,文字浅显易懂,选用简单句式,口语化明显。作者选用字词悉心考虑,惜墨如金,语句十分简练,文白畅晓。海明威并没有把人物当做自身思想喇叭。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选用大量省略和替代用法。用名词、动词、短小句式省略与替代。
场景描写
通过《太阳照常升起》来看,场景描写是整个小说的大纲,所有人物的活动、人物个性展现围绕特定场景进行展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主要铺叙有三个场面,分别是巴黎、西班牙、马德里。
1.巴黎——低沉迷茫与醉生梦死
海明威描写巴黎时选择笔调是低沉的,巴黎场景描写中阐述几位主要人物的关系。这几位小人物每天就是醉生梦死、吃喝玩乐。小说的主要阐述人与杰克都爱着勃莱特。因为杰克在战争中男性部位受伤,不能与勃莱特发生性关系,勃莱特的第一任未婚夫战死在战争中,这让她精神饱受折磨。尽管如此,勃莱特和杰克还是坠入了爱情之海。杰克肉体上受伤与勃莱特精神的损伤注定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完美。
还有其他人物,例如迈克·堪贝尔,勃莱特的未婚夫常年欠债而无经济能力偿还的一个烂酒鬼,比尔戈顿在西班牙节日认识一位美国姑娘,比尔喜欢追求自由,玩世不恭,但却与这位姑娘什么也没有发生。勃莱特是一个泡在酒精里的女人,同时私生活混乱。通过巴黎场景中的人们从多个层面反映出人内心的绝望和对未来生活的迷惘。海明威通过巴黎场景的展现,更多是展现人物多方位的个性,同时也为下面杰克与比尔的西班牙之行埋下伏笔。
2.西班牙——释放自己原本自我生命
杰克和比尔要想逃离在巴黎一切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决定前往西班牙来一次短暂的旅行。这是海明威把场景铺设转向西班牙。在西班牙场景中,海明威用尽全力描述大自然与人类之问和谐相处,场景中充满了自然生命活动。在这里他们在自我迷惘的状态下获得了一丝喘息机会。场景中也描写他们喝酒、但是不是毫无节制酗酒,他们可以游荡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钓鱼、游泳、全方位地放松自己。如此简单,这么快乐。
小说中重点写钓鱼场景,这正是海明威真实情景的写照。海明威一生最喜爱也最为擅长的就是打猎和钓鱼,他每当精神饱受折磨时,他相信大自然可以治愈内心的创伤。杰克和比尔在这几天短暂的旅行中,卸下在繁华都市中虚伪的面具,撕掉了那惯用的冷嘲热讽的语态。他们如同亲兄弟一样真诚对待对方。用真诚坦率的胸怀去向对方打开,彼此尊重,彼此爱护。
当杰克和勃莱特到达西班牙普罗纳时,当地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宗教狂欢节。面对一系列的冲突时,科恩面对斗牛士选择从小说里消失,他的离去标志着迷惘一代在自身幻想式的生活里彻底陷落与失败。与之相反,杰克与布莱顿从年轻的斗牛士感受了面对生死的勇气。
作品影响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成名作,出版以来一直深受有前卫心理和逆反心理、渴望独创艺术、渴望更加开放的心灵空间的年轻读者群的青睐。
出版背景
1920年代是个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跃升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激烈的动荡和混乱的精神,热闹的喧嚣之声处处可闻。而美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丰沛的商品供应,像汽车、家电等日常消费品,娱乐、旅游、休闲等都市生活方式的打造以及广告、媒体等推波助澜,消费主义实际上已在美国赫然耸现。对当时的美国读者而言,《太阳照常升起》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对文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描写。显然这些叙述具有异国情调符合所谓“爵士时代”总的文化气质。符合了美国1920年代消费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
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产生了价值观念上的困境。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在商业繁华如梦的20年代,崇尚享乐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性悖论”。这种因境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价值的观念问题,但实际上是其底层资本逻辑中内在矛盾的体现。一方面,资本增值的生产逻辑要求坚持清教的俭朴、诚实、工作伦理,保证训练有素的工人培养这些良好的品格。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持工业繁荣。另一方,资本增值的消费逻辑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如分期付款、广告、增加休息时间等,鼓励大众积极参与休闲和享乐等消费活动,以便维持欲望的再生产。
作者简介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
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